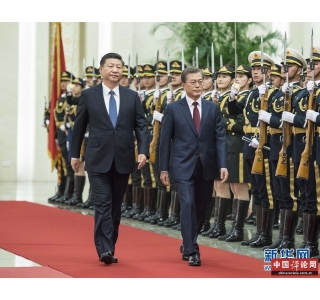欧洲已经帮忙毁掉了英国过去六位保守党首相中的五位: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约翰•梅杰(John Major)以及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这种结果并非欧洲的本意。
当卡梅伦200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时,他希望保守党停止对欧洲“喋喋不休”,以便集中精力应对选民的真正需求。尽管公投结果决定退出欧盟,但不同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决定了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的政治遗产,卡梅伦的政治遗产不大可能由欧洲来界定。
2005年,保守党危机四伏。他们不再是天然的执政党,已经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失利。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是老年人、以及社会地位和居住地稳定的人。少数族裔、学生都厌恶他们。自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工党赢得压倒性多数席位以来,保守党在高校毕业生比例高于平均水平的选区已经失去了优势。截至2005年,保守党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已滑至第三名,落后于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正如特里萨•梅(Theresa May)所指出的,保守党已被很多人视为“讨厌的党”。
当时保守党不仅在社会问题上显得立场狭隘,其作为英国经济合格管理者的声誉也仍未从1992年梅杰政府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中恢复过来。保守党似乎不可能再赢得大选。
卡梅伦改变了这一切。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意识到,保守党只有将经济效率与社会自由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成功。他在2010年经济危机时期上台执政,五年后,英国成为八国集团(G8)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实际上,正是经济上的成功给了退欧派脱离欧盟的信心。1975年首次进行退欧公投之际,英国的经济状况如此之糟,以至于欧共体专员里斯托弗•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警告称,现在不是离开“圣诞储蓄金”的时候,更不用说退出共同市场了。
无可否认,复苏主要集中在伦敦,英国经济仍然非常不平衡。但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提出的英格兰“北部经济引擎”(northern powerhouse)计划——一项对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等都会圈下放权力的激进政策——试图纠正这种局面,同时解决这一“英格兰问题”。
然而,卡梅伦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复苏。他还希望构建一个“大社会”——更平等的生存机会以及一个有抱负的国家。虽然被经济危机和欧洲带离了航向,他仍实现了重大的改革。长远来看,专科院校的扩张以及推出自由学校(截至2015年共建立150所)并改革课程和考试制度,应该能够提升教育水平。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所称的“一般综合中学”的日子无疑完全结束了。
在福利方面,对伤残补助的改革以及延迟通用福利金受到了应有的批评。然而,工作性福利计划使得失业家庭的比例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突出了卡梅伦倡导的社会自由主义。
说到卡梅伦宽容的执政风格,最明显的证据或许是他在政府中创造的良好氛围:一艘快乐的船,这与布莱尔及布朗(Brown)执政时期内阁的争执吵闹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这种良好氛围使得组建联合政府成为可能。许多保守党议员抱怨,比起自己所在的右翼阵营,卡梅伦与自由民主党相处得更加融洽。2015年,卡梅伦或许曾暗自希望再次组建联合政府,而非保守党占绝对多数,而且有可能避免进行退欧公投。
人们更应将政治领袖作为教育家而非立法者加以评判。托尼•本(Tony Benn)曾暗叹道,即便废除撒切尔执政13年间的所有立法法案,她作为教师的遗产也会流传下来。
而卡梅伦将作为一种宽容、文明的保守主义的导师留下他的政治遗产,这种保守主义吸引了中间及中左派选民的支持。去年正是这些选民让保守党自1992年以来首次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从梅在周一发表的演说——强调了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保守主义——来看,她似乎决心继承这种遗产接着走下去。
历史对卡梅伦的评判将比当今评论家之言更友好。正如上世纪60年代保守党殖民地事务大臣伊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指出的:“保守党是一个非常宽厚的政党。它总是宽恕那些犯错的人。有时,它甚至宽恕那些做对了的人。”
本文作者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政府学教授
译者/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