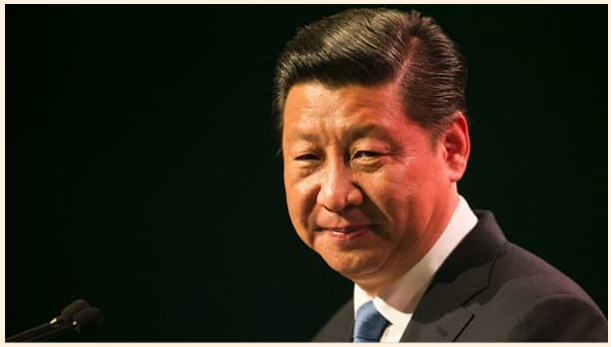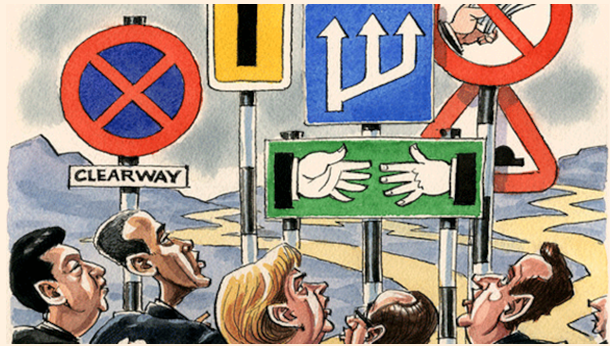如果有人问:大家都感到那些在2017新年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态,标记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该为它起个什么名称最贴切?笔者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没有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
确实,不管阁下高兴不高兴——指名道姓地说谁为此高兴、谁为此不高兴并不很难,只是不礼貌,咱们暂不点名——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是一个缺乏有人敢于出头扛大旗的时代。这种状况发生在1917年那场搅乱了全世界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的今天,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超级悲喜剧。其中饱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的深刻启示,非同小可。
百年之前的“扛大旗”者
整整100年之前的那个时代,与如今正相反:那真是一个有许多扛大旗的有志有胆之士风起云涌的非凡岁月,他们不失时机地乱中挺身、振臂高呼,真诚地认为自己就是历史选定的预言家(The Prophet,更贴切的译名应为“天启先知”),要为全球所有的芸芸大众在乱世中开启一条正当的拯救之道,走向美好而并不遥远的未来。
在以1917年为开天辟地标记的那些敢于扛大旗的人士中,又以列宁和托洛斯基最为耀眼。在他们为当时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深重祸害的苦难众生拟定的重整世界的宏大方案中,对所有那些导致“人对人像豺狼一样、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无比凶残的社会根源,一一提出破解之道。归结到行动实践的层面上,就是:以革命的刺刀铲除民族国家里面“人对人像豺狼一样”的制度根源,以革命的刺刀铲除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国家像虎豹一样”的结构性根源,也即民族国家本身。彻底铲除了保护权势集团利益的民族国家,也就根除了大国欺压小国、发达国家剥削落后国家、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art 2)。列宁和托洛斯基扛的这面大旗,在共产主义运功谱系里被称作“以不断革命(又译为‘继续革命’)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战略,意识形态的术语则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扛出的大旗的对立面,是另一幅大旗——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这幅大旗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出身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籍此在国与国的纠纷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并且最好经由公开斡旋来处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防止秘密外交私下达成肮脏协议,出卖他人权益(E.J. Hobsbawm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译本第49页)。
此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只有一层信念:只要国家之间开放自由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增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风险自然消失,因为一旦开战就会毁掉双方的经济生活血脉。可是,第一次大战恰恰是发生在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时代,交战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密切经贸往来并没有预防大战的爆发。威尔逊力推的国际主义新核心要素,是把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从国别政治普及到国际关系之中,以此来建立和平民主的全球共同体(Alan Cassels,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33-137)。
没有这类强烈信念,不敢出头扛大旗
以上的两面大旗,针锋相对是明摆着的,但细加分析,二者又都具有浓烈的普世主义信念:都坚信自己提出的大方案(即那面大旗)超越了个别民族和国家的视界,不局限于其特殊权益,而是合乎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普遍利益,英文术语表达为两个对立理念: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我们都知道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基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相信美国人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独立、追求幸福这套理想目标,符合人类的天性。美国人之所以经常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指指点点,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受了上帝的旨意,有责任去引领世界各地走上像美国那样的道路,一厢情愿。
列宁和托洛斯基扛的大旗,高扬的是激进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你只要细读他们的原著文本就会发现,其核心是替天行道,尽管这里的“天”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灵,而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的确定未来:他们“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天启般的巨大变化……太平盛世千禧年必然到来”。为了解放全人类,各地的信徒们不分民族、国籍、社会宗派,“都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极端的年代》第105-106页。丁按:作者霍布斯鲍姆14岁在柏林参加共产党,名列最具影响的马克思流派史学家)。
所以,笔者在研习中体认到,敢于出头扛大旗的第一动力,是这样的人信奉普世主义价值,坚信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没有这种“天启我先知”,即自己被选定要在乱世时期为人类指明正确方向的坚定信念,是不会冒大险出头来扛大旗的。普世主义价值的本意,就是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更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集团,而必须是普遍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有最大包容力的价值体系。解放全人类、普渡众生、上帝之城、地上天堂、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千禧盛世,这些措辞不一的提法来自不同教派,透露的是同样的信念。
扛大旗的另一条件
是否坚信自己是普世主义价值的引领人和践行者,决定了他们是否敢于出头扛大旗。但是,大旗能扛多高、尤其是能扛多久,却依赖于扛大旗者拥有的资源是否丰盛及可持续,也就是综合实力的大小长短,因为扛大旗的后面是实实在在的做大事,没完没了。列宁和托洛斯基1917年创立的体系,虽然它集中使用资源的能力举世无双(政治高度集权、经济中央指令),藉此把那面大旗奋勇高扛了一些年头,后来却挺不下去。因为该体系吸血能力超强,造血功能太弱,结果大旗也降下了,体系也崩塌了。
与此对照的是,美国把另一幅大旗却高扛了更长远的时段,它的持续力一来得益于其体系造血功能强,二来其地理位置佳。二次大战结束时,早前的大国和强国要么变小(由于殖民地独立)、要么创伤累累,唯有美国几乎没有受到大损失。多家数据表明,战争期间美国年均GDP增长10%,到了战争结束时,它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5%;到了1950年,它的经济产出是头号对手苏联的三倍多(Christopher
Chase-Dunn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System”, IROWS Working Paper #8, 2002)。正是凭着这样的可持续综合实力,美国才扛着国际自由主义大旗几十年,充当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支柱。然而扛到21世纪初,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不想再扛了,于是就有特朗普这样的人出来大叫:我们不当傻瓜,别的国家各顾各,我们美国也要自顾自。“America First!美国国内优先!”
今年1月20日之后,若是特朗普当政的美国不扛大旗,谁出头扛?全球的政经界和舆论界近来都在建议别国出头,可环球一看,能当候选者的不多。欧盟自身难保,德国能把欧盟挺住就不容易了。普京虽然擅长秀肌肉,但他治下的俄国是一个除了卖原料和军火之外无竞争优势的衰落经济实体。日本是个非正常大国,军力有限人口老化,扛不动大旗。
于是更多的人说,中国现在成了最有希望扛大旗者。这些人士也许只看到中国的GDP总量加上外汇储备(这些数字里有多少泡沫和水分以后再讨论),却忽视了更深层的那个问题——扛大旗者的价值观。如上所述,百年以来凡是在大乱局中敢于出头扛大旗者,都真诚信奉普世主义价值,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唯有提出一套具有超越特殊民族和国家、能够包容最广泛族群和文化圈的价值观,才能引领各国参与建设全球共同体。至于中国有无足够实力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是中国决策层是否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可是,这些年来普世价值在中国是遭到猛烈批判的。
百年以来,是否存在只强调民族国家特色而拒绝普世价值的个人或组织,真能出头扛大旗并朝前迈几步?这个大问题将留待下文细细辨析。不过笔者认为,眼下在扛大旗候选者中,普世主义价值信念和综合实力两者齐备的,好像还看不到——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无人出头扛大旗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乱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